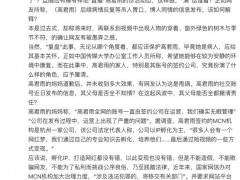县城妈妈陪读空巢丈夫在乡村洗衣做饭
在当下凉山彝族社会,大部分中年女人都有自己的结拜姐妹:她们可能是地理上的邻居,又或者是一起在外打工的人们;也可能是照顾孩子上学的“县城妈妈”,乃至公务员妻子群体。
面对生活的巨大变化和种种困难,她们以这种方式“抱团取暖”,逐渐站上了各种仪式的舞台中心。
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生罗木散在田野调查里专门关注了这一群体,作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以下根据罗木散的讲述整理,部分内容来自其博士论文。
奇女子
我关注到彝族结拜姐妹,是因为一场葬礼,更准确说,因为一个叫伍甲莫的女人。
在我长大的凉山彝族村庄,伍甲莫是一个奇女子。在村里,她总是浓妆艳抹地出现,又不时溜到城里玩,显得无拘无束,村里人称她为“腊人”,意思是不受礼俗约束的混子。
伍甲莫出生于1978年,18岁那年,她失踪了。一同失踪的还有3个女孩,都是村民口中的“腊人”。当年,她们的失踪显得理所当然,在村里早早被判定为离世,成为教训后辈洁身自好的案例。
谁也没想到2003年,25岁的伍甲莫回来了,带着丈夫和5岁儿子,人们才知道她当年被拐到了河南。伍甲莫是被拐者里第一个返乡的,她没有再跟着丈夫回河南,而是留在了家乡凉山。
因为被拐、生育经历背负的污名,她后来嫁给邻村一名贫穷的汉族男人。尽管伍甲莫为人豪爽,在家支各类集体活动中,总是大方招待兄弟姐妹,但始终难以被人们承认。直到2019年,伍甲莫二叔的葬礼上,这个奇女子又一次让所有人震惊。
老人只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几个侄女的奔丧队伍成了当天焦点。(注:葬礼是争夺荣誉的竞技场。按照当地习俗,女子参加娘家葬礼,展演队伍来自夫家家支成员。)中午12点前,其他侄女儿奔丧队伍陆续出场,无论奔丧人数还是抛洒礼物,围观者都十分满意。午后,当众人认为仪式高潮已经过去时,有人传来消息,说伍甲莫的队伍正在集结。
原本退回院子里的人们重新躁动起来,纷纷往门外走去——十几名身着彝族服饰的女性缓缓走来,领头者正是伍甲莫。女人们后面跟着几名男性,队伍最后是一辆大车,拉着一百箱啤酒,走进人群后,队伍大量抛洒礼物。


葬礼上结拜姐妹的舞蹈比拼。讲述者供图
原本人们对伍甲莫没抱任何期待,觉得汉族夫家肯定不会为她组织队伍,但眼前的宏大场面,在场围观者都感到震惊。
这天,伍甲莫的结拜姐妹们卯足了劲,尽情舞蹈,赢下了主人家准备的最高奖金,也赢得了众人赞赏。有人说:“还是这些闯过社会的阵仗大,懂得人情世故”。
这次经历让我关注到“彝族结拜姐妹”的现象。后来我知道,伍甲莫的姐妹中半数以上都有被拐、丧偶这样的经历。当地人总是以“蜡人”贬低她们,“天天在一起喝酒、厮混、逗男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在当下的彝族社会,女性结拜也不仅止于边缘群体。差不多每个成年女性都有结拜姐妹,包括我的母亲,五十岁多了也有结拜姐妹们。除非外出上学的,又或者到了60岁以上才可能没有。
博士阶段在凉山做田野调查,作为论文一部分,我专门关注了结拜姐妹群体,参加她们的结拜活动,观察她们在各类仪式上的展演。我想要搞清楚,她们为什么结拜?结拜姐妹彼此负有怎样的义务和责任?结拜对女性来说改变了什么?
结拜姐妹
外界对彝族的一个看法是,男人一天到晚在喝酒,女人不停在田间劳作。这实际上是一种污名化的评价,来自于对彝族历史的不了解。
彝族两性“分工”确实更为明显,男人们总是将社交之事作为大事,而家庭事务往往被认为只需要女人出马即可,它有历史上的原因——彝族长期面临生存危机,处于半军事化集体状态,男性被视作一个武士,肩负着战斗职责;女性则负责后勤,照顾家庭。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打工潮”来临,男性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留守的妻子开始需要独自生活,结拜姐妹由此而生。
结拜仪式就像彝族平常办酒席,人们一起凑钱杀只小猪,邀请近亲、邻居参加和见证。主桌当然是女人们,通常会有一个带头大姐,举起酒杯说今天大家成了结拜姐妹……之后,她们也会在整个村落里宣扬结拜关系。
传统彝族女性情感非常克制,参加葬礼都不能大声哭,而是以低声吟唱的形式。但结拜姐妹的聚会上,她们纵情饮酒舞蹈。每年,结拜姐妹群体都会组织一到两次的集体聚会,条件好的去西昌,白天游玩夜间烧烤KTV,条件差的就在村子里买些简单的零食、啤酒,展现出支配自我生活意识和能力,完全不同于传统彝族女性形象。

彝族女性引领的奔丧队伍。讲述者供图